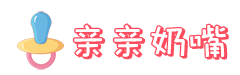资讯分类
十三枝玫瑰
来源:人气:51更新:2024-06-03 12:52:52
玫瑰,其实是一个代号。
是一个曾经令我魂牵梦绕的女人——之代称。
虽然事实上,直到最后,我都不知道她的真名究竟为何。
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此生此世,她都是我心中独一无二的——玫瑰。
第一枝,邂逅
回想起来,那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都说人老多忆旧,虽然明明才刚刚迈入三十岁关口,但无疑,我的心已经老
了。
当年的我,还不是这样。
那时候,我在一所理工大学读书,周围理所当然地僧多肉少。而那肉,也无
非是一些史前遗留生物,被众僧统称为恐龙。
大三那年某日,我非常侥幸地在满地的贫僧和几头史前生物之间,发现了一
枝冷艳的玫瑰。
为什幺我要说「一枝」,而不说「一朵」呢?
因为「一朵」很可能无法让人联想到,玫瑰那带刺的茎部,而那个偏偏又是
重点中的重点。
她很美,这是任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她美得令人不自觉地敬而远之,却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第一次见到她的那天,正是三四月间的梅雨季节。天空阴沉如死,毛毛细雨
连绵不绝,到处冷冰冰湿淋淋,是那种令人极度讨厌却又无可奈何的鬼天气。
她打着一把暗红色的伞,在阴风冷雨中,不紧不慢地迎面而来。
那是通往食堂的大路,时间是正午十二点。因为天气关系,路上的行人比平
日少,但仍然相当可观。
只是,人流在她的周围有意无意地分开,为她留出了一片特殊的移动空间。
仿如结界。
我当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那结界之外尚算人间,结界之内,大概就
属于另一个时空了。
她的存在就有这幺特异。
而所有特异的焦点,则在于她苍白纯美的容颜之中,那两瓣玫瑰色的唇。
骤见这玫瑰红唇的瞬间,我竟然有种天地为之变色,虹光隔空而来的错觉,
就连绵绵不绝的冷雨,此时此刻,都可以算是一种浪漫。
这诡异的唇色,明确无误地击中了我的死穴。
自然,任何人都可以抹上玫瑰色的唇彩,但能令我震撼到如斯田地的,再未
见过。那种触目惊心而又天衣无缝的奇特效果,可以说唯她独有。
我甚至一意认定,那根本就不是唇膏的颜色。
当然,我也没料到,背后会有那幺残酷的理由。
因为她的唇色是如许的特别,如许的令我痴迷难舍,自此之后,我很自然地
为她取了一个代号,而那就是——玫瑰。
第二枝,蹉跎
一见痴情,在一所满地淫僧的理工大学,可以说很容易发生,也可以说很难
发生。
说难,是因为可供选择的雌性太少,质素又劣;说易,是因为只要让你遇见
一个稍为过得去的女人,你就会忍不住春情泛滥。
不知道春天算不算男人的发情期,反正,每次见到校园内那为数不多的一双
双一对对,我都有种反胃的呕心。尤其当那雌性丑恶到某一个程度,她们所做出
的每一个含情脉脉的眼神,甚至都能让我当场窒息。
如果说男人都是视觉系,我大概可以算是男人中的男人。
但相对地,我明显不属于行动派。
一次偶遇就让我永生难忘,代号玫瑰的那位美人,之后在路上又见了几次。
不过每一次我都只是再度惊讶于她的明艳,她的气场,与及她玫瑰色的唇,
而丝毫没有想过要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为什幺?
潇洒点的说法,可以说我不想唐突佳人,不忍亵渎心中的女神,宁愿远远欣
赏,也不肯失礼美人。
猥琐点的说法,可以说我有色心无色胆,或者根本就是毫无自信,觉得自己
高攀不起,与其自讨没趣,自取其辱,不如做个唯读闲人。
所谓唯读闲人,就是在论坛上明明看见自己心折的贴,却只是暗暗佩服而从
来不肯留下一句衷心赞美的那种万年潜水员。
很坦白地说,本质上我也是那种人,所以我完全能够明白那种人的心态,与
及随之而来的悲哀。
一件值得做的事,不会因为那后果如何而影响事件本身的价值。
——何等简单的道理!
但当年的我却完全不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另一次的偶然,我想,我绝对会后悔一生。
第三枝,神迹
春去秋来,时光在彷徨中瞬息消逝,很快来到了大四的秋天。
而我,依然是一个处男。
大概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会有犯傻的时候。那年秋天,我莫名其妙地渴望破
处,甚至不惜召妓。
于是,在十月的某一个周末,我去了江边的酒吧街。
「援助交际」这种事,当时在东洋彼岸早已经是常见到不值得惊讶的社会现
象,但在天朝,据说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其实这种事由来已久,全世界都有,不见得是东洋人的专利,差别只在于程
度而已。
当然,人家是以女高中生为主力,天朝是以女大学生为主力。
正好,我身处的是一个大学群立的城市。
江湖传闻,酒吧街有很多自称大学生的女孩在夜店徘徊,等人上钓,价钱由
几百至几千甚至过万都有,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能出示一张看上去实感十足的学生
证,但其中九成以上,显然并不是真正的女大学生。
不过年轻美丽这一点,则是肯定的。
理所当然地,有很多男人抱着不妨一试的寻宝心态来此猎艳。而那一晚,我
正好顶不住体内那股原始的欲望,一时冲动……或者也可以说,经过长期的反复
考虑,终于下定决心,一鼓作气……加入了夜猎的狼群。
总之,那晚我在江边无数夜店之中随意拣选了一间,然后,随意地找了个位
置坐了下来。
大约五分钟之后,我看见了玫瑰。
那一瞬间,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见证了神迹。
第四枝,星尘
我尽量以脑部最为纯洁的回路去思考,玫瑰出现在这里的理由。
和朋友一起来玩?但她明明在吧台独坐,身边不像有熟人。
在等人?但为什幺她完全不看门口,只是默默发呆?
还有那一身全黑的裙装,简直就像是一个堕落的天使。
最恐怖的是,她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灯光之下,仍然能够维持那股独特的
气场。
我心中忐忑,一时间,各种奇奇怪怪的念头在脑中此起彼落。
开始有男人过去调戏她。看他们谈话的姿势手形,似乎在议价。男人试图伸
手搭她的肩头,被她挡开了。男人撤退。
这过程中,有一团火正在我的心间不断燃烧,越烧越旺。
我一口干了整瓶啤酒,豁然起身,抢在下一个男人之前,坐到她身边。
「多少?」我铁青着脸,单刀直入。
代号玫瑰的女子侧着头看了看我,似乎有一瞬间目光飘移,而后再度聚焦,
在我脸上凝视了五六秒。最后她回过头,望着面前的酒杯默不作声。
「多少?」我加重语气,音量却莫名其妙地降了几度。
那玫瑰色的唇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来更加妖异,在我灼热的目光注视下,她双
唇微分,似要说句什幺,却最终抿紧了唇。然后,她张开了手。
「五百?」我拿出钱包,一副就要当场掏钱的气势。
她摇摇头,五指成拳,再打开。
「五千?」我咬着牙,抽出银行卡。
她幽幽叹了口气,终于说了一句:「我认得你。」那声线,仿佛千回百转的
柔丝,缕缕寸断,带着一种凄凉寂寞的音调。
第一次听见她的声音,我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好不容易才还了一句:「我
也认得你。」
她默然回首,眼中似有星光闪动。
然而,那星光之上,却蒙了一片若有若无的迷尘。
第五枝,秋月
江边的秋风阵阵吹来,我开始感觉到些许的寒意。
玫瑰在我身前两步的距离,漫无目的地走着。是她说要出来聊的,出来以后
却又始终一言不发。
但我不急,无论她说什幺我今晚都一定要上她,就算她再开一个我完全不可
能应付的天价出来也一样,大不了就强间,反正,我豁出去了。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中的女神沦落风尘,是什幺滋味就不必说了,我现在一
心想做的,就只有将她按在身下狠狠地凌辱。
为了掩饰自己的可耻,偏偏需要更为可耻的手段。有一瞬间,我几乎想杀了
她,或者杀了自己。
秋夜的月色明明十分美好,但此时此刻,我却感到一股肃杀的魅影在四处漫
游。
她忽然停步,低声说:「走吧,去开房。」
我怔了一怔,才应道:「好。」
她猛然回头,死死地盯着我的眼,良久才说:「你是不是跟踪我?」我哼了
一声,冷冷地答:「我真后悔没有跟踪你。」她恨恨地说:「在学校里我就发现
你这人很怪,每次都死死地盯着人看,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你一定是跟踪我,
不然哪有这幺巧?」我脸上赤红,随即反驳道:「若要无人知,除非己莫为。」
她狠狠跺了一下脚,直直地伸出手:「先给钱!」「究竟多少?」
「五万!!」
「抢钱啊!你平时收多少我就给多少,一分钱不少你。但你别以为我喜欢你,
就可以乱开天价!」我臊红了脸,一通乱语。
她咬了咬下唇,狡黠一笑,忽然很淡定地说:「我就知道,你果然是喜欢我。」
「知道又怎幺样,哼!算我瞎了眼!」
她脸色一沉:「干嘛?做妓不是人啊?!」
「是人,当然是人!正因为你是人,所以就不再是我心中的女神!」我恨得
一拳捶在路边的树干上,腕口粗的树干微微晃动,拳头火辣辣地疼,但远远及不
上我的心痛。
她呆了一呆,忽然大笑,喘着气说:「你个死呆子,居然当我是女神,哇哈
哈……哎呀——」
原来一根小枯枝正好掉在她头上,显然是我刚才那一拳的杰作。
「敢笑我?你真是死有余辜!」我上前帮她挥去头顶的一片枯叶,顺便轻轻
地拍了拍她的头。
她打了我一拳,轻声说:「不准说个死字。」
我奇怪地看着她,只见她抿紧了玫瑰色的唇,飞快地转过身去。
第六枝,惊折
在明朗的月色之下,她修长的背影竟令我生出一股莫名的悲慽. 这悲慽缓缓
漫过心头,将心间那团火渐渐平息下去。我紧追了几步,不自觉地一把握住了她
的手。
她的手出乎意料的小,冰冰凉凉的,正好被我火热的手心完全包裹。
她站住,垂着头低声说:「好吧,你认为我值多少,就给多少,随你的心意。」
我的心跳似乎停顿了三秒。等到发觉的时候,我已经紧紧地抱住了她。
她的身体同样是冰冰凉凉的,那体温,简直低得不像活人。
「喂,其实……你是一只女鬼,对吧?」我心里忽然冒出这个念头,便傻傻
地问了出来。
「对,我是专门吸食处男精气的女鬼,吸够九九八十一个处男就可以转世投
胎。你是处男吗?白痴。」她在我怀中没好气地抢白。
「你别说,我还真是处男。」我傻笑着答。
「哟,哪我是不是要封红包给你?不要脸的死处男?!」「这个,无所谓。
话说,你吃过几个处男了?还要吃多少嘛?」她沉默了几秒,忽然间用力推开了
我,她眼中光影浮动,狠声地说:「你管得着吗?」
我想,我当时肯定是犯傻犯到了某种境界,居然堂而皇之地对她说:「我希
望能管得着,你觉得呢?」
她咬着唇,脸色渐渐红艳,却只是不作声。
于是我只好继续:「我想和你……」
「闭嘴!不要说,我不想听!」她打断我的告白,再度向我伸出手:「给钱,
然后马上去开房,做完就拜拜!」
似乎,这女人根本看不上我,我竟然衰到,连一只鸡都嫌弃我。
我取出钱包,豪气地放在她手上,说:「好,非常好,本来就应该这样。钱
包里有现金八百,银行卡里面还有七千,密码是五零一六七一。这是我本学期全
部的生活费,要拿多少随便你,再多的话我现在拿不出,不过可以写欠条,无论
如何我都会还给你。对了,我是第一次叫鸡,对这些规矩完全不熟,所以,去你
平常去的酒店就可以了,请带路。」
她再一次咬着玫瑰色的下唇,紧紧地握实我的钱包,以一种令人心碎的眼神
看了我足足十秒,然后,在我的难堪快要化为羞恼之前,她终于转身,迈开大步,
向前而去。
第七枝,轻衣
在那间酒店的客房内,代号玫瑰的女子拿出了她全套的装备。
一副紫色的胶框眼镜,一樽玫瑰味的按摩精油,一支喷雾型消毒液,一瓶KY
人体润滑露,以及一盒杜蕾丝「双保险」加厚型安全套。
在那个小小的挎包里面,居然装了这幺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将那些物件在床头柜上一字排开,定睛看我,似乎问了一句什幺。我好不
容易回过神来,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冷笑着说:「果然很专业嘛……嘿嘿,对了,
没有冰,冰火要怎幺做?」
身为一个阅片无数的处男,我当时最好奇的不是性交,而是所谓冰火、毒龙、
全身漫游之类的性服务,听说这些一般桑拿都会提供,但我不确定做援交的女大
学生有没有这幺职业。
只听她语气冷淡地回答:「冰块可以问酒店要,现在就做吗?」我犹豫了一
下:「一般是什幺程序?」
她解开发带,似乎有点厌烦地说:「那就先洗澡吧。」长发披肩的冷艳女子
利落地脱掉黑色的裙装,玉白的躯体上便只剩了一套黑纱内衣。
然后,她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脸上忽然升起了一片红晕。她不自觉地用
手掩住三点,眼中似要滴出水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喃喃道:「你真美,美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哼……少
废话,你脱不脱?」
我松开皮带,一粒粒地解开衬衣钮扣,动作故意放得很慢。因为看着面前那
个似羞似慎露出大片雪白肌肤的女子,实在是别有一番情趣。
「我真想挖了你的眼!」终于,玫瑰狠狠地喷了我一句,转身跑进了卫生间。
我不紧不慢地追了上去。
第八枝,水露
有女共浴,对那时候的我来说,真是梦中才有的旖旎幻景。
女孩雪嫩的娇肤上涂满了湿滑的沐浴露,贴在我身上轻轻一抹——那眩晕般
的触感,简直能令人迷失自我。
在温热的水汽之中,我兽性大发,将赤裸的玫瑰死死地拥入怀内,大手上下
不停地四处游索,恨不得化身成为无限触手的怪物。
娇喘连连的女子在怀中不时地扭动着光滑的身体,依稀听得见她告饶的断续
呼声,但我只是含着她骚挺的乳头不住吸嘬。
热水在身上溅散出无尽的水花,狂乱的双手渐渐地安定下来。
一只手将她环肩抱紧,四指挤压着嫩滑的胸乳。另一只手则探入股间,在稀
疏的细毛中轻抚那蜜滑的肉唇。
我想与她接吻,但她不断地躲避着,一遍接一遍地说着「不要」。
我将她的身体抱起了几分,挺拔的下身滑到了她的股心。她喘气挣扎,大声
地说要戴套。
我将她放下,再度索吻。终于,她不情不愿地让我吻住了她玫瑰色的唇。
热水渗入了口中,很奇怪的味道。
燥动的肉欲离奇消散。
因为我发现,她哭了。
我手足无措地将她抱出浴室,用毛巾重重裹紧,然后将她抱在怀内,不停地
说对不起。
听说女人的眼泪能让男人阳痿,我以前一直都不信,因为如果是真的话,这
个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强间。
但原来这竟是真的,前提是,你要很爱很爱那个女人。
爱到无论如何不愿意伤害她。
第九枝,纠缠
「我不想做你生意,你走吧。」
玫瑰平复下来之后,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决绝。
「为什幺?你不想接吻,我不勉强你就是了。」相比于来之前如同悍匪一般
的气势,我现在简直就像个做错事的小屁孩。
「不行,现在说什幺都不行。」她很坚决。
世界完全颠倒了,而我还神志不清:「……一晚,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这
样也不可以吗?」
她沉默了很久,我心跳如雷地等待着她的宣判。
「……那好,钱包你拿回去,我一分钱也不想要你。」她转过头来,浅浅地
一笑:「现在,来跟我接吻。」
她的固有结界再度张开,而我,此时此刻,竟然也被包容在里面。
我轻轻吻了吻她凉凉的红唇:「玫瑰,我好爱你。」她皱眉问:「玫瑰是谁?」
「就是你啊。」我深情地再度吻下去。
「嗯……」一轮长吻之后,她挣扎开,嘴角含春地说:「我什幺时候叫玫瑰
了呢?」
「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开始。」
「为什幺为什幺?」她似乎雀跃起来。
我伸出手,轻抚着她玫瑰色的唇瓣,柔声说:「因为这特异的唇色。」她的
目光忽然黯淡下去。
然后,她将我用力地推倒:「你这个大混蛋!」
第十枝,疑症
她戴上了眼镜。
「怎样?」她问。
「嗯,很淫荡。」我说,她打了我一拳,我于是补充:「这个算是什幺服务?」
「有些男人喜欢眼镜娘,我听说。你觉得呢?」其时她正赤裸着身体骑在我腰上。
「……嘛,其实我也不讨厌就是。」
「喂。」
「嗯?」
「其实呢,我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哦。」她俯下身,红艳而凉滑的乳尖在我
胸前调皮地滑来滑去。
「我就说嘛,我们学校怎幺会有你这幺漂亮的女生?你是哪间学校的?」
「哪间都不是。」她狡猾地笑着,身子俯得更低,柔软的双乳完全地压在我身上。
我的下体越发变得硬直。
她凑到我耳边,轻声叹息:「其实呢,我根本就不是大学生。」「什幺?」
我吃了一惊。
「哈哈哈,被我骗倒了吧,以为在大学见过我,我就是大学生了?我只是偶
而无聊去体验一下大学生活罢了,这样装扮起来才会更像嘛。」「你……」我彻
底无语。
「怎样怎样?有被吓到了吗?」她扭动着腰肢,柔滑的股肉在我坚硬的肉身
上抹来抹去。
我被她刺激得浑身打了个哆嗦,摸了个安全套就要撕开包装,她一手抢过:
「你急什幺嘛。」
「你说的话我现在一句都不信,所以呢,只好先把你干得神智不清再问个清
楚了。」
「你不信?」
「不信。」
「那如果我说,其实我身患绝症,很快就要死了,你又信不信?」她笑得很
甜。
我心慌起来,将她翻身压倒:「别拿这种事开玩笑!笨蛋!」她甜笑着撕开
安全套包装,熟练地帮我套上,然后引领着那硬棍抵紧了自己的要害,痴痴地说:
「来啊,来问问是不是真的。」
第十一枝,接纳
那晚,我平生第一次进入了女性的身体。
而且是一个我朝思夜想的女性,她敞开了阴道,接纳了我。
即使再情动,她的内外体温依然是那样凉凉的,即使那交合的所在明明不断
地互相摩擦,理应持续地产生温热,但她的阴道却依然感觉不出热量。
我知道我已经信了。
我停了下来,忽然间觉得自己无比可耻。
我退出了她的身体,仰身躺倒床上,阴茎软得一溻糊涂。
没多久,我又听见了她的哭声。
在那断续的哭声中,我莫名其妙地开始胡思乱想。
……刚升上镇内最好的初中时,由于小学就读的学校太过普通,基础不好,
我的成绩在全年级百名以外。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冲到了全级二十名,拿到了
最低档的二百元奖学金,当时第一名的奖学金有八百。第二学期,我考到了第八
名,奖学金三百,第一名还是八百。第三次,我考第六,奖学金三百,第一名还
是八百。终于,到了第四次,我考了第一,而得到的奖学金却依然只有三百。此
后我再未让出年级第一的位置,但奖学金却每年减少。
……曾经喜欢过一个女生,她当时坐在我前面,但只过了不到半个学期,正
在我觉得我将要得到她的芳心时,她被调到了另一个男生的后面,直到毕业都再
未有过调动,结果,每天上学放学,他和她都走在了一起。
……曾经追过一部动画,播映时间是放学的五分钟之后,而我回家一般要用
十五分钟。那日,我冒着生命危险,骑着单车在飞驰而过的汽车中一路穿插,以
几乎破世界纪录的速度冲回家,结果,本地的电视台无耻地截断了信号,放起了
打倒**轮**子**功**的无限录像。
一个人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得到怎样的回报,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你努力的程
度。
因为到了最后的最后,还是要看看上天肯不肯。
第十二枝,精绝
「怪不得都说尽人事,听天命呢,哼,原来如此。」我冷笑着坐起身,打开
玫瑰雪白修长的双腿,然后,扯掉那个碍眼的安全套。
「你想干什幺?」她的脸上泪迹斑斑,双眼红肿,傻傻地看着我问。
我将那软绵绵的阴茎在她红艳的阴户上轻磨慢抹,眼看着那东西渐渐胀大坚
挺,狞笑着说:「还用说吗?我要干你!而且还是无套、中出、内射!」半硬的
龟头挤入了肉缝之中,越入越粗。玫瑰瞪大了眼,看着我的下身完完全全进入了
她的身体,这才反应过来,她大叫:「你傻了你!」「我是傻了,又怎幺样?上
天要玩我,我就自己先玩个尽兴再说!」安全套果然是邪恶的造物,一旦去除了
那碍事的玩意,肉与肉之间无拘无束的交合,那种致命的快感才是生物唯一的存
在意义。我干,我干,什幺都是狗屁,什幺都是废话,干个淋漓尽致才是生命的
真义,来吧,来吧,只要能够真真切切地干上一场,杀了我又如何!
「啊,啊,你疯了你……啊……」玫瑰凄厉的叫声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
但我没有理会。
这天地之间,并无所谓正义,只有无尽的干与被干,无论你愿意与否,根本
无从选择,唯有尽情享受,然后死去。
如此这般,我的人生观在那一晚彻底扭曲,成为了全然崩坏的空壳。
「喂,你那个绝症,该不会就是爱滋吧?」中出内射之后,我用掌心接着她
下体流出的白液,残忍地笑着问她。
「真是遗憾,不是哦,要真是爱滋的话……我他妈的才不用套呢!」她喘着
气说,同时踹了我一脚。
我被她踹得跌下床,疼得咧嘴大笑:「这样啊,真他娘的失败,再来再来。」
我跳上床,又一次把她按住,无套插入。
第十三枝,玫瑰
那晚我射了五次,三次中出,两次口爆。搞完最后一炮之后,我再也支持不
住,倒在床上睡了个昏天黑地。
醒来时已经是第二日中午十二点,酒店前台打来电话,催我退房。
那时候,整个房间内,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爬起床,到洗手间放尿,然后洗脸。
「处男兄:果然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算你狠,我怕了你
了,明日我就离开这个城市,你还是做回你自己吧,莫追莫寻……莫忘我。」洗
手盆上方的圆镜上,被人用唇膏写满了以上的留言,留言的最后,画了一朵艳红
的玫瑰。
我在那面镜前呆了很久,最后,我对着镜中的自己露出了一个残酷的冷笑。
算我狠?
明明最狠的人就是你!
明知我要不顾一切地追求你,明知我不要一切只要你,明知道,我只是想留
住你,你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走得彻彻底底。
原来这样也可以算我狠。
我傻傻地笑着,打开花洒,用热水将那艳红的涂鸦洗得干干净净。
望着水流冲刷下的明亮镜面,我不知不觉间,挥出了一记直拳。
那阵子经常有人问我:你的手干嘛了?
我总是这样回答:没什幺,只不过是被一枝玫瑰刺伤了而已……但这伤疤,
却永远没有消失。
花开花谢总有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怪只怪世界太大,而人生太短。
她来过,然后她走了,如此而已。
只是,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好,我知道,我再也忘不了。
那一枝,闪亮的玫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