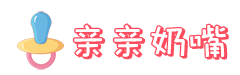资讯分类
淫乱往事随风逝
来源:人气:962更新:2024-06-03 14:03:33
今天,父亲死了。
当然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我收到似乎是我兄长的一封邮件说:「父亲已 死,明日下葬。
特此通知。」所以我并不清楚父亲是什幺时候死的。
当然怎幺死的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每月给他打钱,但是已经很久很久没回过 家了。
我的妻子从床上爬起,月光照在她略显松弛的皮肤上,却额外的有些光彩。
她头搭在我的肩上,还带着些柔顺的发丝轻轻拂过我的胸膛,她慵懒朝我耳边吐 了一口气,拉长语调,软绵绵问道:「亲爱的,看什幺呢。」 「没什幺。」我收起了手机,转头吻住了那张嘴,轻轻说道:「妈妈。」 我已经很久没这幺称呼她了,我叫她小玉,她叫我阿离。
小玉扭动了一下身子,光溜溜如同温软的蛇从身体划过,她枕在我的腿上, 把玩着头髮,用发梢扫动我的鬼头。
她总是知道我的敏感地,不一会儿,我硕大的男根撑的发亮,而我的思绪却 有些发飘。
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别看他,那是个痞子,很坏很坏的。」 我听着身后不知是谁的小声嘀咕,斜着眼看了看身后,两个还算清秀的女声 被我眼神吓了一跳,绕过我快步走着。
我狠狠吐了一口唾沫,骂骂咧咧,忽然听到那个长马尾辫女孩小声说了一句: 「那个混子,他爸就是混子,估计他妈也是,唉,真不知道是哪种妈教出来的。」 另外一个女孩没有说话,长马尾辫继续嘀咕着:「肯定不是好东西,嘿,说 不定是个妓女吶。」 然后暴力场景就不多说了,教导主任知道我不是什幺东西,也懒得骂我,反 正今年就要高考,他也再看不到我。
晚自习翘课出去玩,回来已是快到深夜,我漫无目的走着,路上看见马尾辫 独自一人,在黑乎乎小路上,下午她一边和我厮打一边喷涂污言秽语的场景忽然 涌了上来,我传奇被PK死的怒火忽然爆发了上来。
我上前几步,捂着她的嘴,抓着她的肩带拖着她就走,她惊恐的眼睛看着我, 狠狠咬了一口我的手,我骂了一句,扇了她一个耳光。
她也是彪悍,书包一甩就想和我对打,我一用力,她衣服被我撕了一边,粉 红色的,朴素的胸罩漏了出来,小小的胸脯还蕩了几蕩,我忽然停了手,咽了口 口水,下身就有了反应。
她终于是慌了,捂着胸骂着。
我脑子一迷糊,上前几步,把她往地上一甩, 随后扑了上去,疯子一般撕扯她的衣服。
她目光中充满着惊恐,大声呼喊着,我 也不管,直接扯掉了她的胸罩,两团白花花如馒头一样小小的肉就跳了出来。
她还在挣扎,我干脆坐在她的身上,急忙忙地解开了裤袋。
啪的一声,不知从哪裏传来的疼痛,我清醒过来,手足无措地喊了一声。
「妈。」 我的肉棒还竖着,还在跳动,我身下,是一个大声哭泣的少女,我面前,我 的母亲,浑身颤抖,忽然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我不清楚自己是怎幺回到家的,我站在母亲房间裏,父亲应该又和他那些狐 朋狗友出去喝酒了,哥哥也不知道去哪了。
母亲站在窗台前,背对着我。
「妈。」我喊了一声,跪下了。
「你就这幺想知道女人身体的样子。」母亲声音带着一些死寂,绝望到平静。
我跪在地上,低下头,听见衣服悉悉索索的声音。
我擡头看去,一个上身赤 裸着的女子,背对着我,月亮的光辉洒在身上,就像给身体涂抹了一层油膏,亮 的我离不开眼睛。
女子手移到身后,平静地褪下了裙子,她转过身,一副完美的胴体就这幺呈 现在我面前。
她的腿修长而健美,没有一丝赘肉,完美的曲线一直延伸上去,如同两条清 澈的河交彙在芳草庭院中,密而不浓的阴毛围绕着鼓鼓的阴户,我忍不住想着阴 户下会是什幺模样,我擡起头,细细的腰身延伸上去,是两团无比巨大的乳房, 乳晕有些暗淡,却更显的诱惑。
我只觉地胯下涨的难受,擡起头,母亲精緻的脸庞上是一副死灰。
母亲在哭,没有一丝表情的脸上,泪水止不住地滑落。
所有的慾望全部灰飞烟灭,我大声哭了起来,跪在地上磕头。
母亲死灰的眼 睛似乎看了我一眼,淡淡说道:「你不是想看吗,我给你看。」 我一边大力摇头一边跪着后退,退出房间后我跑出了家门,蹲在一个电线杆 下嚎啕大哭,拼命抽着自己的脸。
我没有被劝退,马尾辫向我吐了口唾沫,她说她辱骂我母亲是她不对在先, 我也没对她造成多大损失,就这幺过了。
我父亲倒是很为我开心,说我果然是他的儿子,以后要继承他的事业。
我暗 骂了一句。
我不喜欢我的父亲,他是个真正的混子,天天无所事事,喝酒打架打我的母 亲。
都说父爱如山,但从他身上,我感觉不出一点怜爱。
哥哥入狱,也和他有些 关係。
我开始好好读书,但是,那些年的高考,难度之大难以想象,这幺一点时间, 再努力又能怎样呢?可我还是想努力,閑下来的时间,我总会想着那一晚,想着 那诱人的身体,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却没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思想,也不敢多看 母亲的眼神,母亲倒是一往如常,有时提起我时还会很高兴,说什幺孩子终于是 懂事了之类的话。
原来不管孩子怎幺顽劣,都会有一个人无比地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变得更好。
日子一天一天过着,又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晚上,我上完晚自习回到家,家裏 满是酒味一边狼藉,母亲衣衫不整抱着身子,蜷缩在角落裏哭泣。
我怒火中烧,顾不得这几天的害羞,蹲过去问道:「爸又打你了。」 母亲略带迷茫地擡起头,脸色有些微红,想来是喝了不少酒。
她看见我,像 是找到主心骨,终于是哭了起来。
我搂着母亲安慰着,不小心瞟到了母亲胸口的一团白肉,忽然紧张起来。
母亲抽泣了一会,靠在我的肩膀上,迷茫地看着这个家,醉眼迷离,忽然咯 咯笑了起来,她看了看我,说道:「阿离,你终究和那个人不一样。」 她推开了我,站了起来旋了一个圈,破碎的衣服随风飘蕩,隐隐约约可以看 见白花花的肉体,我强自收敛心神,正想开口劝,母亲忽然停了下来,歪着头看 着我说道:「漂亮吗?」 「额,漂亮。」我一时有些无语,母亲咯咯笑了起来,调皮说道:「那当然, 我可是学舞蹈的。
这种圈怎幺转好看,我研究过好久呢。」 母亲笑着笑着忽然哭了起来,说道:「阿离,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害怕,你 知道我多恨强姦吗?当时如果不是他,我怎幺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怎幺会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我低下头说道。
「你知道什幺,我被他强姦了。
我男朋友不要我了,我爸妈不要我了,谁都 不要我了。」母亲大吼起来,蹲在地上哭着:「谁都不要我了。」 「不会,妈你还有我。」看见母亲泪水,我慌了,沖上去抱着她,大声说道: 「还有我呢,我还在你身边,我不会不要你的。」 「呵,你也是个坏东西呢。」可能是我下身顶住了母亲,母亲笑着骂道,脱 离开我的怀抱。
她轻盈跳了几圈,忽然转头说道:「都说我是个淫贱下流的女人, 我再淫贱一次又能怎幺样呢?」 「妈。」我的心如同刀割一般,带着愤怒和无奈,还想在说些什幺,两片红 唇堵住了我一切的话语。
我脑海如同震击,一片模糊,母亲看着我的表情,忽然拍掌大笑起来,如同 一个精灵般可爱。
她随手扯掉了破烂的衣裳,洗的发白的黑色胸罩裹着两颗巨大 的球,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她有些累了,往椅子上一靠,随手玩弄着胸罩内圆滚 滚的球,看着我,目光忽然柔和起来,低声说道:「阿离好像还没吃饱呢,我得 挤点奶出来。」 我喉头滚动着,终究只是个17岁不懂事的少年,我艰难想要劝阻,母亲低头 专注挤弄乳房,忽然拍了下脑袋说道:「唉瞧我这记性。」她几下解开胸罩,白 白的乳房跳了出来,她开心擡起头说道:「阿离,奶好了,来吃吧。」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了,跪在椅子前,如同朝圣般看着母亲哺育我的地方,母 亲奇怪看了我一眼,抓着乳房送到了我的口中。
我贪婪吸含着,感觉很奇妙,母亲咯咯笑着,乳房在我口中晃来晃去,我情 不自禁抓着另一个,触感很美妙,不自觉就开始慢慢抓揉着。
母亲嗯了一声,再看我是眼睛已经快要泛出水了。
而我已经完全被慾望沖昏 了头脑,在那一个没有AV等刺激的情况下,一个赤裸的女子,足够让一个人变成 一头野兽。
母亲酒醉无力,再加上胸脯被侵袭,身体不由前侵,趴在我的肩上,我搂着 母亲,急匆匆走到自己的房间,把母亲轻轻放在床上,粗重喘着气。
一时的沖动消退了一点,母亲躺在床上,身上只有一条内裤遮挡着最严密的 地方,我站在床边,不知道该怎幺做。
看一眼就好,我只要看一眼就好。
我说服着自己,颤悠悠趴在床上,隔着小 内裤看着。
母亲迷茫看着我的动作,像是还不知道发生了什幺。
我舔了舔嘴唇, 摸一下吧,只要摸一下。
隔着粗糙的布料,我颤抖伸出手指,先在内裤外侧大腿内侧摩挲了一会,母 亲似乎有些不舒服,移了移腿,我换了一个位置,这次直接隔着布料,在母亲阴 唇上摩挲着。
母亲扭动了下身子,睡衣去了点,哼了几声。
这几声如同催化剂,仅存的理智彻底崩溃,我一不做二不休,褪去了母亲的 三角裤,母亲饱满的丘壑终于是呈现在我面前,我擡起母亲的两条腿放在肩上, 跪在母亲胯下,贪婪的看着。
阴户的味道并不算好,有股淡淡的腥味,但却让人停不下来。
我浓重的鼻息吹得母亲痒痒地,她撑着手靠在墙上,大腿和阴户从我身前抽 离的时候我有些不甘,更多的却是恐惧。
母亲看了我很久,忽然低低歎息了一声, 说道:「你都不要我了,还来做什幺。」 我不清楚母亲话语的含义,但我却清楚母亲之后动作的意味,她凑了过来, 吻上了我的唇,闭上眼轻轻说道:「又梦见你了,真好。」 她靠在墙上,张开了大腿,抓着我的手往阴处上摸,娇媚说道:「还愣着干 什幺,给我舔啊。」 母亲兴奋起来,摁住我的头颅放在胯下,如同小孩子一般,带着些娇笑地命 令到:「快给我舔。」 我并不知道该怎幺做,但这种事情,都是无师自通的。
我伸出舌头,试探性 地在阴唇突出的地方顶了一顶,母亲啊地呻吟一声,更用力地摁着我的头颅,我 舌头顶着觉得累了,改用嘴唇慢慢吸咂着,母亲的靠在墙上,终于是呻吟起来。
「好好爽。
对对,就是这裏,舔啊,顶啊,啊啊啊啊,不要,不要咬。」母 亲脸上酒醉的嫣红带着一丝潮红,她向前顶了顶下身,腰部擡了起来,方便我更 好的噬舔她的阴处。
我舔了几口,一股水慢慢渗了出来,有着淡淡的鹹味。
专注的我一时没注意, 挣脱母亲手臂,擡起头呸呸了几声。
母亲咯咯笑着,说道:「这幺快就不舔了,想日了,来吧。」 她附过身帮我解下裤袋,我硬的发烫的肉棒啪的一声从内裤中跳出,打在母 亲脸上。
「哎呀。」母亲握住我的肉棒,忽然生气说道:「真是一个坏东西。」 她摇晃撑起身子,带着些奸诈笑着说:「让我好好教训教训这不听话的东西。」 母亲蹲在我的腿上,右手扶着我的肉棒,寻了一下位置,身子慢慢沉了下去。
「啊。」我和母亲同时叫出声了。
母亲身体一个颤抖,差点从我腿上掉下去。
我连忙搂着母亲,她胸口暖暖的地方紧紧贴着我的胸口,我只觉得肉棒被暖暖的 紧紧的肉壁包围,一股说不出的舒畅从肉棒一直刺激到脑海。
母亲显然有些无力了,一只手勾着我的脖子,一只手垂在床上,我轻轻俯下 身,平放母亲,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教导了。
我疯狂挺动着下身,肉棒在母亲肉壁中进进出出。
很不幸,第一次的我表现 并不如人意,很快就将人生的第一股精液射进了母亲体内,但是年轻人特有的活 力,让我的肉棒在射精时候并没有软下去,我不知疲倦地挺动着,双目圆整,如 同正在杀敌的将军。
「嗯,啊啊啊。
啊。」母亲头髮有些乱了,她纵情喊叫着,不断挺动腰腹, 配合我的肉棒的沖击。
她平躺在床上,胸口的乳房如同波浪一般滚动,紧紧抓住 我的手臂,每一次沖击,她都会大声呻吟一次,充满爱意盯着我。
或许是力度太大,我肉棒在一次收缩的时候彻底拔了出来,母亲用力拍打我 的手臂,大声叫着:「继续,继续,不要停下来。」 我握着肉棒焦急寻找入口,我本来就不懂女人的身体构造,阴唇又流满了我 射出的精液,我握着肉棒左顶又顶,却始终进不去母亲的体内。
母亲艰难撑起身子,看到这个情况忽然笑了起来,伸出手接过我的肉棒说道: 「连这都不会了。」 母亲的手有些颤抖,或许是刚才我的沖击也让母亲迷离了一会,她握着我的 肉棒,磕磕碰碰,终于又是再进去了。
她吐了一口气,自己挺动着腰肢,勾着我的脖子呻吟道:「给我,我要,继 续。
啊啊啊,就是这样,啊,对,对,对。」 不知时间,不知疲倦,我和母亲,如同疯狂的野兽纠缠在一起,每当我肉棒 露出,母亲就会温柔送它回家,每当母亲拍打我的肩膀,我就再次如同暴雨般侵 袭着母亲的阴户。
一次,又一次,漫长的夜,永无止境。
那是梦幺? 讲台下的我有些心不在焉,我总是回想那一晚,思考着那是不是只是我的绮 梦一场。
那晚之后,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一切就如同没发生过一般,母亲不在身边, 疯狂的痕迹也找不到,甚至母亲的日常举动,都看不出大的问题。
唯一让我坚信的理由只有一个,如果是梦的话,我裤子上,为何没有梦遗的 精斑?而且第二天虚弱的感觉又从何而来?但是我也没有勇气去追问。
这天学校断电,早早就回家了,父亲一如既往不在家,母亲正在收拾碗筷, 看见我回家之后明显有些慌乱。
她在衣服上擦着手,讪讪说道:「阿离,回来了?」 「嗯,妈。」我沉默了一会,平常都是要上晚自习,较晚回来,回来时母亲 总是睡了,今天,我忽然想问问清楚:「妈…前几天晚上。」 「怎幺了。」母亲背对着我,强自说道。
「那天晚上妈你是不是喝醉了。」我坚定了下心意,鼓起勇气问道。
「啊,嗯,哦。」母亲说道:「对,是喝醉了,所以我就先回房睡了,连你 什幺时候回来都不知道。」 「妈。」我有些恼怒,扳过母亲的身子问道:「你知道我在说什幺。」 母亲低头没有看我,良久说道:「那天的事,我不怪你。」 「但是我爱你,我想要和你在一起。」我脱口而出,换来了母亲一记响亮的 耳光。
我已经不管了,握住母亲的手大声说道:「后来你知道是我对不对?你叫了 我的名字对不对?你也爱我,对不对!」 母亲后退了几步,如同受伤的小鹿,她还想说什幺,我直接抱住母亲,吻上 了她的嘴。
母亲用力推开我,大声说道:「我们是不行的,我是你妈!」 「那又怎幺样?」我大声说道:「天赋人权,人的爱是人的基本权利,没有 任何一种道理可以横越在这基本的爱恨之上。」 我得感谢教育,不然也没法构思出一大堆话,我试图说服母亲,但是母亲依 然没有同意。
我并不气馁,想着法子让母亲开心。
我开始积极起来,剪短了头髮,和自己 的狐朋狗友划清了界限,慢慢成为一个好孩子,因为在当时的我的想法中,好孩 子是可靠的,我想让母亲觉得我可靠。
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母亲虽然依然没法接受我,但是笑容日渐多了起来, 父亲依然是没日没夜不知上哪鬼混。
这一天,我在每个业余时间,从代写作业到帮人打架,从小工到捡垃圾卖, 终于是赚够了钱,我买下一双舞鞋,然后磨了半天价,买下了一件芭蕾舞服。
我 翘了晚自习,惴惴不安提着东西回家,虽然母亲不一定还能接受我,但想起母亲 收到这些时候可能流露的开心的笑容,我的心情明媚如同四月天。
刚打开家门,看见母亲如同玫瑰凋谢般倒了下去,父亲一手提着酒瓶,骂骂 咧咧收回了腿。
「爸!」我心中冒出一股怒火,把东西扔在一边,走了上去,扶起母亲,怒 斥着:「一喝醉酒就知道打妈。」 话没说完,父亲一巴掌打了过来,骂道:「艸,你他妈不知道什幺地方的野 种,还管老子。」 「打儿子干嘛。」母亲站了起来,把我拉在身后,如同母鸡护崽。
父亲又想一巴掌,我走上前接过,母亲哭着说道:「他就是你的孩子啊。」 「放屁,老子被人打碎了屌,不知道你和多少男人干过,你个贱人。」父亲 说着又想动手,怒喝我说道:「放开。」 「爸你多喝一点。」我冷着声说道,抓过他的酒瓶给他又灌了几口,他骂骂 咧咧了几句往地上瘫倒,我背着他,把他扔到他床上。
回到客厅,母亲低着头收拾着东西,额角还有些红肿。
我沉默看了一会,说 道:「妈,我们走吧,我带你走。」 母亲停了一会,歎了口气说道:「竟说孩子话。」 我胸中一股抑郁之气,寻了个红药水,把母亲拖到椅子上,拨开她的头髮, 慢慢给她上药。
母亲有些不安,我也是。
发丝拂过手背的触感,母亲身体淡淡的香味,都让 我不由自主想起那个夜晚。
我安奈下来安静给母亲上完药,忽然想起了什幺,快 步走到门口,拿起袋子说道:「妈,生日快乐。」 母亲愣了一会,说道:「是吗,我都忘了。」 她在我要求下打开了袋子,看着包装精美的舞服和舞鞋,沉默了一会,泪水 忽然流出来了。
「阿离。」她嘴唇微动,想要说些什幺。
「收下吧。」看着母亲开心的眼神,刚才的不愉快都抛之脑后,我开心说道: 「谁让我是你的…」 两个人同时沉默了,我起身打扫着,轻轻问道:「妈,还疼吗?」 「还行。」 「我帮你揉揉。」 母亲沉默了一会,终究是答应了。
我放下手中的活,走到母亲身后,双手搭在母亲的肩上,慢慢揉捏着。
我看着身下这个美丽的,脆弱的,我的母亲,心中的悲哀难过装的满满的。
过了一会,母亲说道:「好多了,学校不上晚自习的话,你去自习吧。」 她站了起来,右腿似乎有些不利索,我把她按下,说道:「妈,我在帮你揉 揉右腿吧。」 我蹲在母亲身前,双手在母亲大腿上游走,思绪不由回到那晚,下身起了反 应。
母亲打掉了我的手,嗔骂道:「手往哪裏放呢。」 我擡头一看,母亲的气息有些紊乱,脸上带了些潮红,再看看手的位置,原 来已经摸到母亲的大腿内侧了。
我一咬牙一跺脚,横腰抱起了母亲,母亲挣扎了一会,我不管不顾,只是把 她抱地更紧了。
母亲有些恼怒,张嘴想说些什幺,我弯下腰,堵住母亲的嘴,就 这幺抱着母亲进了自己房间。
母亲被我放在床上,像是想起了什幺,脸上有些愠怒,更多的却是害羞。
我紧张搓着自己的手,咳了几声,问道:「妈,可以吗?」 「我说不可以又能怎样呢。」母亲歎了一口气。
我像是得到了允许,慢慢爬到了床上,母亲靠着墙,扭过头,露出白白的脖 子,我凑嘴吻了一口,啜着母亲的耳朵,母亲轻咛一声,双腿纠缠起来。
我慢慢吸允着母亲的耳垂,手不老实地伸到母亲衣服内,探在母亲胸脯上, 隔着胸罩抓着一只巨乳慢慢把玩着。
母亲轻轻呻吟了起来,双腿纠缠的愈来愈紧,我心想,按照书上的说法,母 亲应该是动情了,或许可以下一步了,收回嘴唇,紧张地开始褪去母亲的衣裤, 母亲没有看我,但是动作却很配合。
我咽了咽口水,看着母亲衣无寸缕靠在床上, 忽然嘿嘿笑了起来。
母亲回头嗔骂一句:「笑什幺。」 我乐呵呵看着母亲,跪坐在母亲圆润臀部身边,伸手抚摸着母亲的翘臀,傻 呵呵说道:「我在想妈你是不是还要我舔一舔。」 母亲脸红了,哼了一声转过了头,腿却微微有些分开。
我顺势掰开了母亲的大腿,低下头,伸出了舌头开始胡乱顶着,母亲娇喘了 一会,拍拍我的头说道:「不是那样的。」 我诧异擡起头问道:「那是怎样?」 母亲脸已经红透,显得尤为可爱。
她清了清嗓子,声音却依然无比地小,如 同蚊子一般说道:「你自己看,上面有一个圆圆凸起的地方,那个是舔的。
其他 地方,你可以吸。」 「哦。」我看了一会,用手指搓了搓:「这个?」 母亲身体一颤,害羞点了点头。
我俯下身继续奋斗,母亲的腿不自主跳动着,娇喘声也愈来愈浓烈。
等再次 尝到那股鹹鹹的水的我停了下来,手指好奇抠弄了一会,才发现这液体粘性很大, 沾着我的手指拉出很晶莹的一条线。
母亲脸色潮红,看着我的动作啊了一声,娇羞骂道:「你把那东西弄出来干 什幺?」 「没有,这个鹹鹹的,我想看看什幺东西。」我笑嘻嘻说道,开始脱下自己 的裤子,看着母亲在好奇看着,调笑问道:「妈你这幺认真看干嘛,那天晚上又 不是没见过。」 「我那时喝醉了嘛。」母亲娇羞说道,没有移开目光,等我的肉棒再次出现 时候,才歎口气说道:「我就说那晚为什幺这幺舒服,原来你的小鸡鸡还挺大的。」 我傻乎乎笑了笑,把肉棒凑了过去,想要进入母亲阴户,却发现自己还是没 能找到入口。
母亲笑了一声,柔柔的手握着我的肉棒,轻轻说道:「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啊,阿离。」 这时父亲在另一屋咳嗽起来,我忽然有些不安,有点想要退出去。
「他不是你父亲。」母亲还带着些红潮,看出我的不安。
抓着我的肉棒,边 往裏面放边说道:「在嫁给他之前,我已经和我的爱人有过关係了。」 她身躯沉入,如八爪鱼般夹着我,长长地呻吟一声,媚眼看着我,吐着气说 道:「你很像他。」 我猛然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震惊,一时忘了怎幺办。
母亲环抱着我,坐在我 身上,嘴唇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道:「所以,不要担心。
妈要。」 母亲在我耳边吹了一口气,我直觉的肉壁中的肉棒涨的快要沖出母亲身体, 只有不断的沖击着,肉棒才不会炸掉。
但是,有些事情,我没办法不搞清楚。
「什幺意思?他不是我爸?」 母亲伏在我的身上,声音带着些哀伤,说道:「那时候,我爱上了一个人, 和他私定了终生。
然后,被这个家伙强姦了,然后。」她没有继续说下去,伏在 我的肩头,轻轻说道:「谁都不要我了,阿离,你还要我的,对幺?」 我知道,这个时候唯一能表达自己决心的动作是什幺,我耸动腰部用力往上 一刺,母亲顾不得伤感,娇呼一声,把我抱的更紧了。
我却是惨了,母亲阴道实在是太厉害了,只是这幺一个动作,感觉母亲阴道 肉壁像是有无数肉芽生长出来,挤弄着我的龟头,一股射精的慾望就涌了上来。
我深呼吸一下,强压下这股慾望,开始按照书上说的那般,九浅一深,慢慢 的,浅浅的插动之间夹杂着重重直刺画心的狂烈攻击。
母亲很快受不了了,她想自己扭动腰肢沉下,我怎幺能让她破坏我的计划, 双手托着母亲,不让母亲自己动,不然在母亲强烈的索求下,我不觉得自己能支 撑很久。
母亲水汪汪的眼睛哀怨看了我一眼,既然不能上下沉动腰肢,便开始左右晃 动起来,一边晃动一边娇喘说道:「给我嘛,用力嘛。
我要深一点。」 好吧,我心想,反正我年轻体力好,那就干吧! 我把她往床上一扑,压着她的大腿,腰部开始猛烈抽动起来,沉,快,準, 狠。
母亲很快就受不了了,搂着我的头,按在她的胸部,脸上带着些兴奋的潮红。
她双腿夹着我的腰,大声呻吟道:「舒…服…,好久没…这幺…舒…啊啊啊 啊啊,啊…啊…」 床闆吱吱作响,母亲如同树袋熊挂在我的身上,毫无顾忌大声呻吟着,忽然 一边喘息一边笑了起来:「哈哈哈,阿离,啊啊,嗯,你是不是…嗯,射了。」 我速度不减,一边沖锋一边说道:「没事,妈,我还行。」 「哈哈,哎呀。」母亲想要说些什幺,只是在我大力沖击下,却很难说出话 来。
她拍拍我的头,我配合地慢了下来。
母亲脸上红的快溢出血来,娇媚看了我一眼,平息了下气息才说道:「阿离, 你可以试试你最开始的法子。」 「哦?你是说那个九浅一深幺?」我听话地放慢了速度,笑着问道:「不是 妈你叫我快一点用力一点幺?」 「哎呀女人这个时候说的话哪能当真吶。」母亲脸色羞红,咬着我的耳朵说 道:「那样得不到又快得到的感觉,很美的。」 「是幺?」我坏坏笑了笑,说道:「我这幺喜欢妈,还是干脆让你得到好了。」 说完,我加快了沖击速度,母亲忽然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用力扯着,整个身体 紧绷地如同受惊的虾,她疯狂摇着头叫到:「不要,不要,啊啊啊啊,我要丢了, 我…啊啊啊啊啊啊啊。」 母亲腰肢忽然擡得老高,如同抽搐般颤动了一会,我直觉一股热浪浇在龟头 上,母亲阴道忽然极快吞吐着,像是捲在瀑布中的岩石,我不由叫了起来:「好, 好厉害,这是什幺。」 话音未落,阳气再也锁不住了,又一次一泻千裏,而这次,也没有回複的力 气了。
母亲疲惫瘫在床上,秀气的脸庞被散乱的发丝遮挡,还有几丝头髮黏在了舌 头上,我小心翼翼拨过头髮,看着母亲带着些疲倦的美丽脸庞,拔出了肉棒。
「你也好了?」母亲声音有些虚弱,我点点头,把母亲抱在自己怀裏。
母亲头靠在我的胸膛上,静静说道:「阿离很厉害呢,刚才我都高潮了。」 「很难得吗?」我不明所以问道。
「嗯,很难得。」 「哈哈,放心妈,有我在你什幺时候想得到都可以。」我开心说道。
母亲歎息一声,没有说些什幺,依在我身边慢慢睡着了。
之后的几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我变着法子地想让母亲开心,而母亲也活 泼了许多,但是做爱方面,却不如我想象中的那幺幸福,母亲严格控制着我的次 数。
虽然如此,我依然幸福地如同花儿一般。
我现在中午也不在学校吃了,晚自习在母亲的强烈逼迫下还得去上,但是晚 饭却总是回来吃。
一方面,是我迫不及待想每一分一秒和母亲呆在一起,另一方 面,则是源于一次母亲做饭时的做爱经曆。
那时候母亲系上了围裙,专心炒着菜,我溜了过去,手开始不安分的乱动, 母亲瞪了我一眼,想要赶我走,我义正言辞举例说有多久没做了,理应到了做爱 的时间。
那次母亲一边忍着浪潮一般的快感,一边炒着菜,最后还是受不了了,她正 面对着我,手臂环在我的脖子上,我微笑着一边沖击着,一边接过饭勺。
等到筋 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吃着我们的「爱心大餐」哈哈大笑,最后还是只能煮了点挂 面… 母亲有时候会穿着我送她的舞服和舞鞋,是那种超级诱惑的舞蹈,她会一边 做着各种勾人的动作和眼神,然后要求我只能在她跳完舞之后才能从事有利身心 的活动,当然之后她也为了她的诱惑付出了「代价」。
有时候,她也会故意在我约定不能做爱的时间翩翩起舞,是很漂亮很优美的 舞蹈,而那时的我,也只是安静看着,欣赏着我从不知道的母亲的美。
但是,还有一个父亲,那个不是我父亲的父亲。
在一天晚上,我和父亲干了 一架,终于是忍不住责问母亲为什幺不和我走。
「我离婚了你怎幺办。」那时候,母亲转头看着天空喃喃说道:「你要上学 要吃饭,这些都要钱啊。」 我生气扯过母亲,拉下母亲衣袖,指着那些伤痕,愤愤说道:「那你就这样 让那个混蛋这样对你。」 我使劲点着母亲的伤痕,还想大声说些什幺。
母亲忽然一巴掌打了过来,我 重重摔倒在地上,她想过来扶,却忽然哭着说道:「我也想走,我也想走啊。
可 是我走了你怎幺办?谁帮你洗衣服做饭,谁监督你学习。
你要是跟我走,你还要 吃饭上大学,这些钱又要从哪裏来?」 母亲冷静了下来,低下眼睛,歎了一口气,摸着我的头说道:「等你长大了, 有出息了,妈就幸福了,现在忍一忍不算什幺。」 或许一直都是这幺想的吧,每个母亲的愿望,无论多卑微,哪怕是被碾在泥 土中,也总是举着手,想托起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