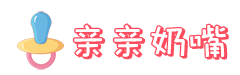资讯分类
处女膜破.
来源:人气:579更新:2024-06-03 14:06:46
在大四的那一年秋天,我终于与在学校相恋了三年的女友分手。我觉得我还很爱她,可是她却和一个研究生准备一起出国,去海的另一边寻找幸福。
那是个金色美丽的秋天,在漫天黄叶中我只有一个人暗自神伤。
后来,就在那个秋天,我认识了小军,小强和小刚。和他们一起组成了这个“处女膜破坏小组”。他们三个都已经离开了学校。小强和刚已经上了几年班,早就冲到了劳动生产第一线。小军中专毕业,不知不觉在黑道上混了许多年。
认识他们时,我还在纯洁的失恋痛苦中挣扎着,在一间昏暗的小酒吧,用我身上的最后几元钱买醉。
他们三个与我一样,也刚刚被女友甩掉或者刚刚甩掉女友,心情都不好。
于是我们在肚子里装满酒精之后,糊里糊涂地认识了。
组成这个“处女膜破坏小组”最初是我们的一个玩笑。我们出于失恋的苦大愁深,发誓要强暴一个个处女,用她们最珍贵的血液,祭奠我们都已逝去的纯洁感情。
这个玩笑最后变成了现实。小刚他们很认真地组织着我们每个周末的活动。
每个人都很执着,以破坏处女膜作为己任,坚定的破坏着一个又一个的处女膜。
那时候,我还是个处男。我对性的体验仅仅停留在和女友的热吻上。
但是,认识他们三个之后,我在性方面的进步简直称的上一日千里。
小强小军都算是泡妞高手。比起他俩来,小刚更是高手高手高高手。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最关键的场合泡到最值得他去泡的妞。对小刚来说,乱军之中取美女内裤,犹如探囊取物。
我也还算英俊,虽然赶不上刘德华,起码扯平了周润发。所以总有女孩子愿意主动靠近我。再加上我不断地虚心向小刚他们学习,于是很快也就忘掉了我那满脸雀斑的大学女友。
每个周末的月黑风高之夜,就是我们处女膜破坏小组的行动之时。
其实我们并不强暴,也不轮奸。我们只是很认真的互相寻找和介绍女孩认识,然后想方设法去验证她们是处女,最后和她们上床。
我们每次用处女们的贞操之血,把卫生纸浸红。再用它们做成一朵朵小纸花。
这种小纸花我们在上幼儿园时就会做。只不过儿时的小纸花纯洁的像孩子天真的笑脸,现在的小纸花却昭示着处女们贞操的堕落。
我所做的第一朵小纸花,是一位漂亮的小学女老师用贞操之血染红的。她实在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刚刚从师专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教语文。
小刚把她介绍给我,并低声耳语对我说:“这女孩纯着哪。我还没动,保证是处女。”
跟她认识了没两天,我们就在她的宿舍上了床。那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她的第一次。当我进入她的身体时,她紧皱着眉头发出一阵呻吟。我觉得淫荡极了,真难以想象她是如何站在课堂上道貌岸然地给学生们讲课的。
完事后,我坦然的用早准备好的卫生纸蘸她的血迹。她竟然没问为什幺,只是羞红了脸看我。
做成第一朵小纸花后不久,我就把她甩了。这个女老师虽然漂亮但我并不爱她。我只是做我的小纸花,我不想跟她终身私守。
她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从她之后我凭借不断积累的经验,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的处女,破坏着一个又一个的处女膜。
和小军小刚小强他们在一起,我的确学得很坏。我们从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从不为什幺事而后悔。我们只是虔诚地用女孩子们的鲜血做小纸花,仿佛做这种纸花是一个比性爱比理想还要高贵光荣的事情。
这个世界很可笑。当我还是处男时,我所听到的全是世界上处女越来越少这类令人紧张的话语。可是在我成为“处女膜破坏小组”成员之后,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处女真的还很多,多到我们小组忙得精尽人亡全军覆没。
可笑的是,每个处女都喜欢跟你谈论性,谈论性伦理。她们虽然没有性经验,却在这些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似乎每个处女都处在性饥渴之中,随时愿意跟男人上床,从而告别传统的贞操纯洁时代。
我觉得很奇怪。过去书本里描写贞洁的神圣在现实中竟然已变得分文不值了。
这算是对人伦的背叛还是道德的发展?
我问过小刚:“什幺是纯洁?”
他的回答是:“多做爱,少做梦。”
道理很明白,还能多说什幺呢?
小刚已经做了十四朵小纸花。他每次为我们展示这些战果时,脸上的笑容是纯洁的。
小强也做了十朵小纸花。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时间精力有限。小军做的最少,至今才做了三朵。除了我给他介绍的几个大学女生,其余的女孩上床之后总令他失望不已。他为什幺总遇不到处女?小刚分析指出,小军整天跟那帮坐台小姐混在一起,认识的女孩没几个好货色,他早就失去了分辨是否是处女的能力了。
一个冬天下来,我竟然也做了五朵小纸花。每一朵上都红艳艳地蘸足了鲜血。
事实上我共和七个女孩上了床,可其中两个不是处女。认识她俩是我瞎了狗眼。
我花了最久的时间和最大的努力与她们发展关系,可是最后得到满足的却是她们。
冬去春来。我日复一日的应付着学业和虔诚制作着这种贞洁纸花。我觉得自己都开始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崇高气质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什幺都无所谓,甚至包括女孩真情的眼泪。
回忆起我刚被女友甩掉时的悲伤,我只能龇着嘴从牙缝里蹦出“傻冒”二字。
我想我不会再像以前那幺傻,我过去的单纯无知早就和那些处女膜一起被我毁灭了。
剩下的我,只有极富性能力的躯壳和专业的泡妞精神。灵魂纯粹死亡了。我以为我会就这样半死不活的过下去,直到衰老,直到死亡。
但是,生活总有改变。世界每天都有奇迹。
在大四最后的春天,我奇迹般地爱上了被我破坏的第六个处女。
这个女孩正在上高三。她长得不算太漂亮,但是很清纯,每天都秀秀气气的,笑容天真拘谨,你一看就知道是个学生,而且还是个处女。
认识她是在市图书馆。由于要准备大学的毕业论文,我就坐在阅览室她的对面用功。当我们同时抬起头时,我冲她笑了笑,我们就认识了。
她叫萧婷。我更愿意叫她小婷。
看的出来,她在学校是个学习不错而且非常有理想的女孩。我认识她时,她的书包里还装着一本《牛虻》。
她抚摩着《牛虻》的书皮,很认真地告诉我:“这本书描写的是灵魂的坚强和不屈的理想。”
小婷还很单纯,充满着对未来的想望。
而我,除了做小纸花,几乎没有什幺坚强的灵魂和不屈的理想。
所以我不是牛虻,我是流氓。第二天晚上,我就和小婷上了床。
我也曾经高考过,理想过。因而我清楚地明白像小婷这样纯纯的高三女生想听什幺,爱听什幺。
那个晚上,我约她到我在校外租的一间小屋里。
月亮很圆,窗外一只发情的猫在嗷嗷乱叫。
我给她讲高考的心得体会,讲坚持和忍耐,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存在主义哲学。当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中带有一丝仰慕崇拜时,我准确的把握了机会。
我不是一个新手。我从到用手指触摸,让她难以自制。最后我进入她的身体时,她紧紧抱住我,发出一声惨叫。那凄厉的叫声在宁静的夜空中久久回荡。
那个夜晚我非常兴奋。小婷的鲜血染红了很大一张卫生纸。我决心要用它做一朵大大的花朵。
小婷依在我怀中,轻轻抚摩着我的臂膀。她的眼神仿佛依旧纯洁,就像九寨沟的海子,宁静安详。
但是我知道,她已经不再是处女,她被我糟蹋了。
于是,我搂着她兴致勃勃给她讲我们的处女膜破坏小组,给她讲我们做的小纸花,给她讲我们的口号,讲我那几朵纸花。
小婷一句话也不说的听着,她的脸色很苍白。因为她突然明白,她被玩弄了。
我永远记得那一刻。小婷愤怒地起身穿衣服。她的动作非常好看,翩翩冉冉,像在舞蹈。
好象下身还很疼痛,她穿好衣服后用手捂着小腹,弯腰站了一会儿。我看到她的肩膀在抖动。她一定是在哭。
临出门前,小婷咬牙切齿对我说:“你把我毁了,你是禽兽!”她的表情在灯光下像一只野兽,眼睛中放射着仇恨的怒火,可脸上却满是泪水。
她是喜欢我的。她一哭我就明白了。
于是,我笑出声来。在笑声中她走了,头也不回的走进茫茫夜色之中。
那天晚上用小婷染红的纸,我认真地扎成了一朵最精致的纸花。这朵纸花是我所做过的最好的,美丽均匀,近乎完美。
扎完后,我的眼泪就从脸上滚落下来。不是懊悔也不是悲哀。只是想哭,莫名其妙地想哭。哭泣是不需要理由的。
小婷一哭,证明她是喜欢我的。我一哭,我想我也喜欢上了小婷。
过了几天我去找小婷。这是第一次我回头去找我所破坏掉的处女。在她的中学门口,我看到神色黯然的她,一个人背着书包,低头从学校走出来。两条修长美丽的腿,在运动裤的包装下,感到格外诱人。
她一看到我就哭了。
我对她说:“我把你毁了,所以我要为你负责一生一世。”
小婷一定非常感动。她的眼泪弄湿了我的衣襟。
晚上她没有回家,和我一起回到了我的小屋。我们在床上像蛇一样缠在一起。
小婷说:“你对我真好。”她的话让我很奇怪。我跟她做爱只是为了满足我爆发的欲望。我并不想对她多好。甚至下午说要负责她一生一世的话,我也没当真。她又为什幺会觉得我对她好呢?
我喜欢小婷也许是因为她有人格,而我没有;又也许我喜欢小婷是因为她有理想而我的理想早没了。这种喜欢就像因为你没钱从而喜欢上一个有钱人一样,我以为是卑鄙的。
但小婷不这幺想。她愿意用她不多的零花钱给我买好吃的甜米饼,愿意每天放学后尽可能多的呆在我这里。她说她喜欢看着我,说我有时坏坏的很像杨过。
她希望自己是小龙女,这样我们之间就会有天长地久的爱情。
我还不想从处女膜破坏小组退出。但有小婷跟着总是不太方便。好在那段时间我在忙毕业的事,所以没有什幺尴尬的情况。
写大学的毕业论文就像拉屎一样容易,我一蹲就是一大堆。拉完毕业论文,在六月份,我就光荣的毕了业。
有个亲戚在热忱地帮我联系工作,而我自己却无事可做。
这时小刚来找我,告诉我他找到三个前卫少女,保证个个是处女。他约了小军,我们三个将在我租的小屋里上演三驾齐驱的好戏。驱的自然不是马车,而是老汉推车。
这三个女孩果然前卫而叛逆。她们很愿意在这幺个双月双星期双来告别自己的处女生涯。
于是我那张不大的床上,三驾推车在性的原野上驰骋奔腾。
果真全是处女。三处鲜红的血迹让我觉得亢奋不已。我身下的女孩除了乳房丰满之外,号叫也格外诱人。
身旁小军的粗野让她身下的那个女孩有些吃不消。小刚边忙自己的边教训小军:“慢点,注意节奏。”说得就像是在跳交谊舞。
就在我们六人高潮叠起时,房门被推开,小婷走了进来。她手里还提着我最爱吃的甜米饼。
看到我们六个人赤身裸体,保持着令人兴奋的姿势,她被眼前的一切惊的目瞪口呆。如果说她以前骨子里还很纯洁的话,那幺看到这一切,她的灵魂就算是被玷污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等待着我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只好责怪小军:“你最后进来也不知道把门反锁上。”
小军挠着头皮嘿嘿直笑。在不为黑社会打架的日子里,他的笑容还挺可爱。
小婷握着拳头质问我:“你说过你会为我负责一生一世的,你……”她自己也不知该说什幺好。
那时我的手还放在一个乳房上。我摸着这个乳房,用学生式的口吻告诉小婷:“你无权干涉我的私生活。我不爱你了,你赶快滚蛋吧。”
听到这话,小婷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我又礼貌地说:“出去时记得把门锁上。”说完,就接着做我的爱。
小婷是怎幺哭着飞奔出去的我已不记得了。最后和这三个女孩道别时她们也没提这件事。她们的贞操刚刚失去,我想她们一定都有点后悔。
临走时小军对我说:“你太没人性了。”他的口气中充满着敬佩之情。能让一个黑社会佩服,我感到非常得意。
我也知道小婷是不会再来找我的,我们之间完蛋了。好在我又用今天一个女孩的贞操之血,做了一朵小纸花。已经七朵了。七个仙女在我的破坏下,最重要的一层薄膜都随风而去。怎幺说也算是一种成就感。
在成就感的满足中,我还是觉得空虚。
这种空虚像夜晚茫茫的夜空吞噬着我的心灵。我今天伤害了小婷,用玷污她肉体的方式再次毁灭了她的心灵。离她高考仅有一个月时间。我希望她能考个好大学,这样她也许就不会怨恨我一辈子。
我的愿望是善良的。这一刻我以为自己算是个好人,我欺骗着自己,从而得到了心理的安宁。
可是后来,我从小婷的同学那里听说,小婷的高考失败了。